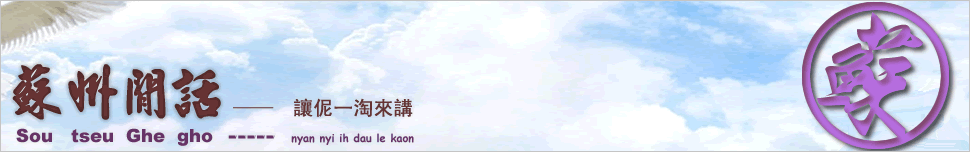转自<名城苏州网站>-http://www.2500sz.com/
苏州方言的文化延伸,构筑独特的苏州文化景观,在歌谣、戏曲、小说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都得到深刻的反映。胡适在《吴歌甲集序》里谈到吴语文学时说:“吴语文学向来很少完全独立的,昆曲中的吴语说白往往限于打诨的部分,弹词中也只有偶然插入苏白,直到近几十年写倡妓生活的小说,也只有一部分的谈话用苏白,记叙部分仍旧用官话。要寻完全独立的吴语文学,我们须向苏州的歌谣里寻去。”
苏州歌谣以吴歌为代表,吴歌虽然广泛传播于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,但苏州则是主要的区域,顾颉刚《苏州史志笔记》引《渔矶漫钞》就称“吴歌惟苏州为佳”。吴歌的起源很早,陆侃如在《歌谣》二卷二十八期撰文,认为最早的吴歌是《诸减锺》,产生于公元前七世纪;二百年后的《左传》中有近《楚辞》的吴歌;最早的越诗《越人歌》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,它也属吴歌。《战国策》记楚国使者陈轸对秦王说:“今轸将为王吴吟。”“吴吟”究竟是徒歌还是乐歌,虽然无可稽考。但《楚辞·招魂》的“吴歈蔡讴,奏大吕些”,则可见当时就有合乐的吴歌。左思《吴都赋》也有这样的咏赞:“幸乎馆娃之宫,张女乐而娱群臣。罗金石与丝竹,若钧天之下陈。登东歌,操南音,胤《阳阿》,咏《 任》,荆艳楚舞,吴愉越吟,翕习容裔,靡靡愔愔。”寥寥数语,说出了早期吴歌的特有情调。千百年来,吴歌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,由三字句而四字句、五字句、七字句,它那“靡靡愔愔”的抒情方式,则更与叙述内容完美结合,委婉清丽,温柔敦厚,含蓄缠绵,隐喻曲折,如涓涓流水,柔韧而含情脉脉,正是吴侬软语在歌曲中表现。
从文献记录来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吴楚汝南歌》十五篇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的《吴声歌辞曲》一卷,都是保存在乐府中的吴歌,只是经过文人润色,甚至改作,失去了原有的土膏露气之真。然而吴歌的表现形式受到历代诗人的青睐,颇多摹仿之作,如杜甫《愁诗》就自注“强戏为吴体”,许印芳《诗谱详说》称“当时吴中歌谣有此格调,诗流效用之也”。这种拟作的诗歌,后人也称“吴体”或“吴歌格”,汲取了吴歌的天真自然的养分。但是舍本求末,流传于民间的吴歌却未被重视,很少有人去作本色的记录,故较罕见,如宋人《京本通俗小说》卷十六《冯玉梅团圆》引了一首:“月子弯弯照九州,几家欢乐几家愁,几家夫妇同罗帐,几家飘零在他州?”并称“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间,述民间离乱之苦”。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吴歌。明昆山人叶盛的《水东日记》,也记录了这首吴歌,还另外记了一首:“南山头上鹁鸪啼,见说亲爷娶晚妻。爷娶晚妻爷心喜,前孃儿女好孤凄。”并说是“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,多作讴歌以自遣,名唱山歌,中亦多可为警劝者”。明太仓人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也记了一首:“南山脚下一缸油,姊妹两个合梳头。大个梳做盘龙髻,小个梳做扬篮头。”这种记录是可珍贵的。
明代苏州“唱山歌”的风气兴盛,不少文人认为当时诗歌创作已趋衰微,吴歌的清新活泼却显示出独有的魅力,贺贻孙的《诗筏》、王骥德的《曲律》、凌濛初的《南音三籁》等称吴歌“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”,“修大雅者反不能作”,卓珂月甚至称为“我明一绝”。明人传奇往往采用吴歌作为插曲,民俗杂著如《游览萃编》等也间或选录吴歌作为附载,可见它受到市民百姓的欢迎,在民间有广泛的欣赏群体。这时的吴歌,杂体大增,有唱有白,有衬字,有缀语,这在《六十种曲》《白雪遗音》《霓裳续谱》诸书中可见一斑。
明人辑集吴歌最早的知见刊本是《适情十种》(别本总题《破愁一夕话》),所收浮白主人选吴歌六十首;另外还有《雅俗同观》卷六收醉月子选辑的《新锓千家诗吴歌》六十一首。《适情十种》扉页题“明冯梦龙原辑,明卞文玉重辑”,可见浮白主人所刊是以冯梦龙辑本为底本的,惜冯氏辑本失传已久,直到1934年,上海传经堂主人在徽州访书时才发现了明刻写本《童痴二弄·山歌》,题作“墨憨斋主人述”,这正是冯梦龙所辑的原本,后经顾颉刚校点刊行,这部沉埋约三百年的“苏州歌谣的大总集”方重现于世。
《山歌》收录的作品,绝大部分采自民间的“矢口成言”,冯梦龙在整理过程中,加工改订不大,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面貌,这在冯梦龙的评注中可以得到证明,如卷一《私情四句》的第一首《笑》:“东南风起打斜来,好朵鲜花叶上开,后生娘子家没要嘻嘻笑,多少私情笑里来。”冯注道:“凡‘生’字、‘声’字、‘争’字,俱从俗谈叶入江阳韵。此类甚多,不能备载。吴人歌吴,譬诸打瓦抛钱,一方之戏,正不必钦降文规,须行天下也。”这不仅是有关记录吴音的说明,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搜集、整理的原则。这与冯梦龙的美学观有关,他认为诗歌有“真”“假”之分,这些民间流传的“山歌”,“情真而不可废”,属“民间性情之响”“郑卫之遗”,即使色情猥亵者,也是“真”的反映。这种对民俗现象的态度是严肃的。
《山歌》共十卷,前九卷用比较纯粹的苏州一带方言记录,方言系统比较纯粹,颇能反映当时苏州一带的方言面貌。最后一卷《桐城时兴歌》则用蓝青官话记录,这些桐城地方曲调也曾在苏州一带流传。《山歌》保存了一部分明代苏州的方音、方言以及方言字的的资料,有的冯梦龙在评注和眉批里有所说明。首先,通过排比、分析各首的韵脚用字,可归纳当时苏州方言的韵类,进而构拟音值;其次,《山歌》记录的方言词有三百五十个左右,其中有一部分是现代不用的历史词汇,如第三人称单数用“渠”,现代苏州用“俚”,由此可以了解苏州方言词汇的演变;再次,《山歌》前九卷共收二百三十七首吴歌,包括一千以上的句子,分析这些句子可以了解当时苏州方言的语法结构。《山歌》提供如此丰富、纯粹的方言材料,这在明代以前的文献中是罕见的。另外,《山歌》又保存了许多明代市语,有的有冯梦龙眉批,如眉批《山人》,有“光斯欣,市语,犹言光棍”;眉批《烧香娘娘》,有“白银曰放光”。更多的则未予注明,如银子称“白脸”“冰玉”,钱称“黄边”“嘉靖”“孔方”,纸称“萧山”“富阳”“包扎”“薄光”,只堪一用的称“一出货”,指桑骂槐称“借名凿字”等等,这些都是吴语研究的珍贵资料。《山歌》还提供了丰富的明代社会风俗史料,如卷九《杂咏长歌》的《鞋子》《破骔帽歌》《烧香娘娘》等篇,与范濂《云间据目钞》卷二《记风俗》里的有关条目相参证,对明代苏州一带的生活习尚可得到更真实、生动的了解。《山歌》里的部分吴歌传播久远,如《十六不谐》至清代仍流行,嘉庆十六年(1811)刊《双玉杯传弹词》也曾引用,儿歌《萤火虫》则民国年间尚在里巷间传唱。
1918年,北京大学的部分学者发起征集歌谣,顾颉刚以苏州歌谣的搜集、研究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,刊印了《吴歌甲集》、《吴歌小史》等,吴歌的现代研究由此而开始。《吴歌甲集》的编集,受到同仁的推崇,纷纷撰序。胡适说:“《甲集》分为二卷,第一卷里全是儿歌,是最纯粹的吴语文学,我们读这一卷的时候,口口声声都仿佛看见苏州小孩的伶俐、活泼、柔软、俏皮的神气。这是‘道地’的方言文学。”“第二卷为成人唱的歌,其中颇有粗通文事的人编制的长歌,已不纯粹是苏白的民歌了。其中虽然也有几首绝好的民歌,——如《快鞋》、《摘菜心》、《麻骨门闩》,——然而大部分的长歌都显出弹词唱本的恶影响:浮泛的滥调与烂熟的套语侵入民歌之中,便减少了民歌的朴素的风味了。”沈兼士说:“现在颉刚搜集的吴歌,虽不能说是尽是有精彩的技巧和思想,但那种旖旎温柔情文兼至的风调,总不能不推它为南言歌谣中的巨擘。”俞平伯说:“吴声是何等的柔曼,而歌词又何等的温厚,我们若是搭足绅士的架子忽略它们,直是空入宝山,万分可惜。在此不得不感谢颉刚编次之功了。”刘半农则认为“民歌俗曲中把语言、风土、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”,“自从六朝以至于今日,大约是吴越的文明该做中国全部文明的领袖罢。吴越区域之中,又大约是苏州一处该做得领袖罢。如果我这话说得不大错,那么苏州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处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不料中国人无人不爱玩苏州,而求其所以爱玩苏州梦寐难忘者,无非是寒山寺的钟声,虎丘山的香冢;其下焉者,则玄妙观前吃板茶,金阊门里骑驴子,把天上无双人间不二的吴侬《白苎》之歌一扔扔到了青旸港里。这不但是苏州人要气昏,便是我们附庸于苏州的人也要愤愤不平”。由此可以看出顾颉刚的贡献来。
此外,1928年李白英辑成《江苏情歌集》,1933年林宗礼、钱佐元辑成《江苏歌谣集》,后者收三千余首,其中约一千首是吴歌。除对吴歌作搜集、整理外,吴歌演唱活动也引起学者关注,顾颉刚在《苏州史志笔记》里就记了几条,说“月子弯弯照九州”一首,“今吴中操舟者多歌之。当更阑夜静,风细月明时,倚篷注听,殊使人意思凄感”。又一条记道:“陈万里告我,渠幼年住苏州乌鹊桥,每于夏日晚上,听夹河男女两队唱‘对山歌’,自抒己意,出口成章。按此与广西歌墟无异,男女对唱,无论为择偶或文娱均极自然,而苏州亦有此风,则我所未知。”从中也可看到吴歌与苏州民间风俗活动的关系。
迟至民国年间,苏州郡城及常熟等县仍有“唱春”的风俗。这大凡在正月里,有唱春者,头戴红结瓜皮帽,身穿布长袍,左手执小铜锣,右手以木片敲击,在大街小巷沿户卖唱,所到之处,视店铺或门第大小,以吉祥语编唱歌词,也有唱十二月花名的。所唱以方言出之,语调轻松,委宛可听,听者乐于布施。这也可视为吴歌的别裁。
值得一说的是长篇叙事吴歌,同治七年(1868)丁日昌查禁“小本淫词唱片”,就有《薛六郎偷阿姨山歌》《赵圣关山歌》《沈七哥山歌》《杨邱大山歌》等,它们带有明显的唱本化或小调组合化痕迹,后期的如《五姑娘》等,已与狭义的清初唱本有所区别,运用了诗的手法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苏州民间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热情对《五姑娘》等作了采集和整理,但如何保留其原始面貌和风味,仍需要深思熟虑。
**请各位朋友尊重的作者的版权,如果我们不慎侵犯了您的版权,请您及时联系我们,我们也会立即做出回应。